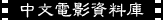德国经典影片回顾展
德国经典影片回顾展,本来不想去了。结果,对门的女孩问我“你去吗?”, 又莫名其妙的想去了。怕赶上开幕式讲话,不想早去;又怕错过开头, 不敢晚去,犹犹豫豫,七点一刻到了礼堂。台上姿态各异地站了一排人, 为首的德国高个儿正在讲话。我一听就乐了,又是歌德学会, 去年和露天社办过德国默片展的。转到楼上坐下,等着《三毛钱歌剧》的开始。 余下的讲话倒蛮有意思,几个电影界领导都跟台下套近乎, 纷纷自报家门说是清华校友,最后一位清华领导来了一段德文祝词, 而这就是我整晚最有趣的经历了。
而后的影片,至少对我而言,是乏味的。 包括介绍时说很有名的那一场大群乞丐在女王加冕仪式时拥上街头的戏, 从头至尾我都没有什么感觉,几乎完全是出于一种习惯性的不半途而废坚持着。 如果我坚持看完,我想,至少我能明白它为什么叫《三毛钱歌剧》。 但是我错了,除了几次既长又不算动听,总能促使几个人离开的唱歌之外, 我一点都看不出这部片子和歌剧有什么关系。电影结束时, 本来就人丁稀少的楼上只剩我一个人了。我扫视了一下空荡荡的座位, 终于有了点阿Q式的自豪感,在第二个电影开始前离开了。
我觉得真正的问题并不是时间和地域,和它常常莫名其妙停滞不前的呆板镜头, 或是那有时跳变得吓我一跳,有时又磨蹭得让我失去耐心的剧情。 如果它能有一两个画面让我有所感动,哪怕仅是有点感觉, 我都可以对其它一切视而不见,高高兴兴地做“睁眼瞎”;或者干脆爱屋及乌, 觉得这些都很可爱。一部影片能称其为经典,总该是有些什么能抓住你的; 然而不知为什么,我始终是一个漠然的旁观者, 始终清醒地知道那一切发生在银幕里,而我坐在外面。 我怀疑我最终想去是因为想起了《浮士德》——去年五月, 德国默片展开幕式那天放的第二个片子。我以为一部默片都能给我留下美好的印象, 何况更近的呢。不过事情并不总是如人所愿的。
《浮士德》是一部挺可爱的片子,现在想起来还止不住要对自己笑。 模模糊糊还记得那天现场钢琴伴奏的外国老头,好象是个秃头, 围了耀眼的红围巾。翻译字幕的人语调很有趣,“啊,格蕾辛”, 他大概是想尽量贴近剧情的感觉,要感情充沛,却有点力不从心。 电影里的人幼稚的飞来飞去,让我想起月球旅行记里一头扎在月球上的大炮弹。 魔鬼梅菲斯特一本正经地撕着向日葵的花瓣, 念着:“她爱我,她不爱我......”但真正印象深刻的是它的结尾, 被彻底篡改了,忏悔的浮士德冲到行刑现场救下了格蕾辛, 然后在棉花堆一样的云层中出现了光辉灿烂的上帝, 钢琴也无比光辉灿烂起来。“爱情战胜了一切”,翻译说。 我通常不喜欢这样的篡改的,可是当时感动死了, 因为那种粗糙但又朴素的真挚。无论是之前还是之后看的一些真正金碧辉煌的片子, 都没有那样光辉灿烂的心情。后来我试图对同学形容当时的感觉, 但找不到合适的词,我说就是感觉特别膨胀。她就笑。
后来的一次露天沙龙,提到《香港电影双周刊》上发的一张照片, 据说每一个热爱电影的人看到都会感动的。主人公是我们内地的一个很年轻, 却颇有一番闯劲儿的导演,租不起移动轨,他就扛着摄像机, 站在一辆板儿车上,被别人拉着拍电影。不知怎么, 我就想起了浮士德里飞来飞去的人。
执着和挚爱,总能让我感动。人的感情真是顽强, 总是能从粗糙和简陋的表面中渗透出来。我喜欢人拍出来的, 为给人看的电影。看到总有一些人,没有被日常琐碎麻木掉,还在思考着, 还在敏感地注视着周围,还在感动和被感动着,就觉得很幸福。